媒体:面临校园暴力的孩子 该拿什么保护?
时间:2017-01-20 09:44 作者:小波 点击: 次

1月18日,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“肥西一中学女生遭校园暴力,被逼下跪磕头”的爆料视频,视频中一女生跪倒在地被逼迫磕头,下跪期间遭受另外几名学生扇耳光、被脚踹等行为。据报道,涉事学生所在学校介绍说,此事因双方女学生间为“找回面子”所致。目前公安机关已认定此事非校园欺凌事件,不予立案。
作为一名孩子的家长,虽然自己的孩子一直被保护得很好,但看到类似的校园暴力视频时,笔者还是心痛不已、紧张不已。对于弱小、善良、无辜的孩子来说,当他们面对无法抗争的外在暴力时,内心该有多恐惧、多紧张;而未来,当我的孩子进入小学、中学后,她是否会得到足够的保护,是否会暴露于校园暴力的危险之下?我并不确定。这种紧张感不是学校承诺可以消除的,它取决于社会对此有没有总体性的制度保护。
这一点,可以从个案的处理和应对中看出。遗憾的是,在以往关于校园霸凌的个案处理中,我们几乎看不到制度层面的反思。对于已曝光的校园霸凌事件,当地总是习惯以危机公关的思维应对:一方面,把校园霸凌事件当成是一个需要应对的危机,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,各方想的是如何安稳地度过这个危机,而不是彻底地解决问题;另一方面,他们把转移舆论视线当成是危机应对成功的标准,只要这次危机暂时度过了,即使问题没有解决,也没什么关系,反正同一地方被曝光的概率极低,反正下一次即便有类似事件曝光,那也是别人的事情。
于是,在校园霸凌事件的处理中,经常会出现舆情诉求和地方表态的反差。在公众看来,被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足够触目惊心,按照人们的生活经验,说其是校园霸凌一点也不为过,所以必须给予严厉的处罚;但是在地方看来,所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总是有过度描述之嫌,其实质不过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的打闹而已,只需加强相关教育即可。结果,不断出现的校园暴力事件持续冲击着舆论的承受力,人们对学校等应对者的失望也在同步剧增;相反,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反而没有人关注,甚至人们连什么是校园霸凌都说不清楚——请问,认定标准在哪里?视频都如此暴力了,为何还不算校园霸凌?
这是制度性思考缺失的必然结果。在校园霸凌的制度应对中,有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必须梳理清楚的:校园霸凌的认定和预防体系是否存在;校园霸凌的应对和处理制度是否存在;校园霸凌的惩戒和教育机制是否存在。只有这三个层面的制度都完善了,人们才可能在一个校园霸凌事件发生时,心平气和地应对——制度会对这个校园霸凌事件作出应有的纠正。而不是担心校园霸凌事件在学校各方的遮丑心理中被掩盖下去,或者在各方的不知所措中被轻易地放过。如果真是这样,社会所面临的结果,只能是校园霸凌事件的层出不穷。
校园霸凌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,而且十分复杂。但即便如此,应对和解决校园霸凌问题的最好办法依然是完善相关的制度,并对个案进行制度性纠错。这是无法绕过的制度路径。唯有如此,一个触目惊心的事件才能成为严峻的现象,才能引起社会的真正重视,成为社会的公共议题。相反,如果在面对校园霸凌事件时,总是不把它当回事,或是总想着怎么撇清干系,那么校园霸凌现象就会一直存在并且恶化——个案的价值不过是瞬时的刺激罢了。
无论是围观的公众还是处理校园暴力事件的各方,在新的校园暴力事件出现、曝光后,都应该追问一句:我们的制度完善了吗,我们拿什么保护可能面临校园暴力的孩子?他们是视频中被伤害的弱小者,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。
相关 · 新闻
近日,随着“北京中关村二小”事件的持续发酵,关于如何定义“校园霸凌”?被“霸凌”后该如何处理?网络上议论争论不休。
“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,对于校园霸凌家长都要求强烈处理,但在学校里和学生接触最多的老师,最该保护学生的老师却对欺凌、霸凌不以为意了。”一名广州的家长在讨论校园霸凌时呼吁,抵制校园霸凌,得让学校先重视。
12月22日,记者采访了多位中学班主任和中学心理咨询师。这些教师来自中国多个省市,既有上海等大都市的教师,也有欠发达地区。
对于“校园霸凌”,有受访教师表示无法定义,“学校从没和老师讲过什么是校园霸凌,老师该如何解决校园霸凌。无论学校还是老师,从未把‘校园霸凌’当作一件事”,而面对发生的“校园霸凌”,学校则往往是“息事宁人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态度。
也有受访教师指出,如今家长过于溺爱孩子,对于“校园霸凌”一方面很担心,另一方面,对于自己的孩子欺负别人,则抱着“反正我的孩子没被欺负”的心态,置之不理。
还有受访教师呼吁,家长们在关注“中关村二小”事件、声讨“校园霸凌”时,除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受欺负,更应该反思,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欺负过别人。
多名受访教师表示,更重要的是,“校园霸凌”应当引起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重视,将“校园霸凌”列入规章制度里,一旦发现,予以严惩。
内容导航
相关阅读
- 09-06牙疼但又在备孕期还能吃止疼药吗?
- 09-06阿胶浆适用于备孕女性来调理吗?
- 09-06备孕期跑步对身体有益吗?
- 09-06宝爸备孕时要不要吃叶酸,也吃碱性食品吗?
- 09-06有什么药可以帮助调理受孕儿子的吗?
- 09-06利 动治疗便秘效果好吗?
- 09-06朋友介绍去佐嘉医务中心验男女,有去过的吗?
- 09-06HK抽血查男女 ,哪一家路线最简单?
- 09-06香港验血具体路线有知道的吗??
- 09-06香港验血几周验才准??
- 09-06想知道姐妹们是为什么选择英国奶粉?
- 09-06儿童咳嗽声音嘶哑,咳嗽怎么办呀?
- 09-06想给宝宝换一种口味清淡的奶粉,挑了一些想去买美素佳儿金装的,结果发现他
- 09-06姐姐生小孩了,想给宝宝选一款奶粉当做礼物,有什么质量好口碑好的奶粉品牌
- 09-06见红了还未生是怎么回事啊?已经建红四天了怎么还是没有动静
- 09-06格蕾菲娜祛妊娠纹多少钱一盒?
- 09-06格蕾菲娜祛肥胖纹和妊娠纹怎么样?效果好不好?
- 09-06格蕾菲娜祛妊娠纹肥胖纹效果怎么样?真的好用吗?
- 09-06格蕾菲娜祛妊娠纹怎么样真的能祛掉吗
- 09-06格蕾菲娜祛妊娠纹GreyFina真的有效果吗?求真相!
- 09-06什么奶粉好?什么牌子的宝宝奶粉不上火?
- 09-06有谁知道进口奶粉排行榜10强?宝宝奶粉哪个牌子比较好?
- 09-06幼儿湿疹怎么办?
- 09-06给宝宝挑选奶粉要注意哪几方面?
- 09-06奶粉排名榜里的雅士利品牌怎么样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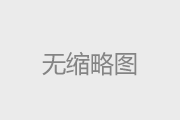 大小球必胜公式-足球财富:滚球中大小球必杀技适合各
大小球必胜公式-足球财富:滚球中大小球必杀技适合各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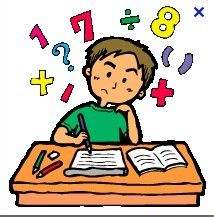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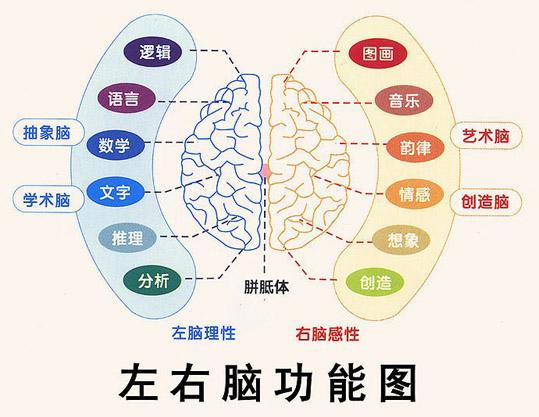
 怀孕后就不能吃这些?医生说:别闹了,让
怀孕后就不能吃这些?医生说:别闹了,让

